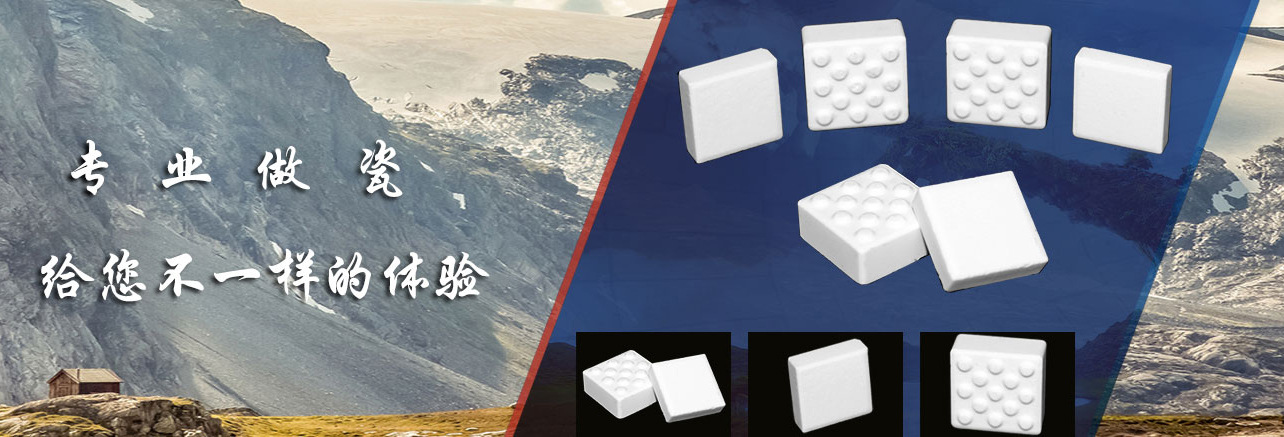一组承载着民国时期风云变幻的老相片,使用前沿技能,精心修正上色。这些相片记录了特别年代的日常,是研讨民国前史的宝贵一手材料,见证了年月变迁,宝贵程度显而易见。
民国的街头,喧嚣熙攘。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蜷缩在街边的街沿上,双眼直勾勾地紧盯着自己手中的鸟笼 。


民国时期,养鸟之风盛行,这一喜好自清代八旗子弟 “提笼架鸟” 的遗习演化而来,至民国已深深融入估客日子。《故都杂咏》中就有 “街头羽客各争妍,紫燕黄莺笼底翩” 的生动描绘。其时,北平城表里鸟市热闹非凡,据1935年《北平习俗类征》计算,仅前门外廊房头条的鸟市,每日成交额可达数百银元 。
民国北平琉璃厂西街,一辆改装推车上,推车主人缩着脖子坐在车辕上,双手揣在袖筒里取暖。他面前摆着蒙灰的瓷器、铜炉、钵盂等物,他应该是那种古玩估客。

这样的活动摊位在民国北平并不罕见。据《故都文物略》记载,1930年代的琉璃厂周边活泼着数百个打鼓儿的,他们走街串巷收买旧物,再易手倒卖。

摊子上的瓷器多来自天津锅店街的仿古作坊,铜器则出自前门打磨厂的老匠人之手。最抢手的是棺材板货——从古墓中盗掘的冥器,经过做旧处理后身价倍增。曾有古玩商回想,1935年琉璃厂某摊贩以三十块银元收得一只战国错金银鼎,易手就以三千大洋卖给了日本商人,这笔横财满足普通人家十年的开支。
1934年深秋的北平琉璃厂西街,一男人正踩着八卦步舞枪,补丁摞补丁的月白短打衫随动作翻飞,肩肘处的灰布补丁已磨得发亮,显露底下粗麻布的经纬,却是枪杆上绑扎的红缨穗子般艳丽。


这样的场景,在民国的街头巷尾并不罕见。那些补丁摞补丁的衣衫下,藏着的或许是镖局身世的落魄镖师,或许是武馆关闭的教头,他们用祖传的把式在年代的夹缝里讨日子。
1940 年,广东蕉岭新铺镇的一隅,凌维诚带着四个子女,在韶光中留下了这宝贵的合影。


这张相片的拍照者,是回乡探亲的中山大学教授钟敬文。他在日记中写道:“凌夫人言语不多,唯指其子女曰‘均能背诵父亲信件’,继民当场朗念书札‘倭寇未灭,何故家为’,声如洪钟,惊飞檐下麻雀。” 事实上,自1937年谢晋元撤入租界后,凌维诚便带着子女从上海迁回蕉岭,谢绝了全部政府补助,靠变卖陪嫁品和田产度日,每日亲身教子女习字,讲义就是谢晋元寄来的《正气歌》手抄本。
1929年10月,广州,26岁的上尉教官谢晋元身着笔挺的黄呢戎衣,正牵着新娘凌维诚的手,正在完结结婚仪式。

凌维诚来自广东蕉岭的书香门第,与谢晋元是同乡。1925年谢晋元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时,她正在县立女子中学就读,两人经过信件树立联络,一起的家国情怀让互相招引。1929年,谢晋元从南京中心陆军军官学校结业,留校担任战术教官,总算在战乱空隙定下婚期。

证婚人、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在致辞中说:“今天之婚礼,当以‘执子之手,与子同袍’为训,望贤伉俪既修两姓之好,更守报国之贞。” 这番话后来竟成预言——七年后淞沪会战迸发,谢晋元率部据守四行库房,凌维诚则带着三个孩子曲折后方,饯别着“嫁与武士不望归”的坚韧。
1937年10月31日清晨,姑苏河上的薄雾没有散尽,谢晋元率四行库房守军残部423人(对外称“八百勇士”)分批撤入公共租界。这支打退日军11次进攻、据守阵地四昼夜的英豪部队,此时正踩着浸满硝烟的军靴,跨过架设在河面上的“垃 圾桥”(今西藏路桥),却不知道等候他们的不是友军的喝彩,而是英军黑洞洞的枪口。


依据《九国条约》规则,交兵两边不得在租界内驻军,但英军以“避免抵触扩展”为由,违反中立准则,要求勇士们“暂时解除武装”。时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费信惇的备忘录记载:“日军要挟若不放行,将轰击租界,我方不得不退让。” 清晨3时,官兵们在河南路桥堍被逼交出步枪400余支、机枪20挺、手榴弹千余枚,仅保存随身匕首。谢晋元在日记中痛斥:“吾等以热血看护之疆土,竟无容身之处。”
1933年3月,长城喜峰口的硝烟染灰了春日的晴空,我国第29军官兵正依托残缺的敌楼与垛口阻击日军。


枪管在北风中发烫,大刀在白刃战中卷刃,年青战士们用身躯将 “一寸山河一寸血” 的誓词刻进长城的青砖 —— 这里是冷武器与热武器交错的战场,更是中华民族永不曲折的脊柱。
这张抗战相片中的我国战士半蹲据枪,手里是捷克斯洛伐克ZH-29半自动步枪。该枪由伊曼纽尔·哈力克1928年规划,选用导气式原理,具有半自动射击功用,射速40发/分钟,射程800米。


1929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东北军购入150支ZH-29及100支改进型ZH-32,粤军陈济棠部也收购33支ZH-32。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沈阳东三省兵工厂拷贝出“辽造十三式”,年产约50支,曾用于1933年长城抗战。全面抗战中,ZH-29因弹药适配问题未大规模列装,但在淞沪、徐州会战中可见于中心军精锐部队。该枪全球产值约500支,除我国外,100支售予埃塞俄比亚用于抗意战役。
谢晋元头戴德式钢盔的个人照,是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四行库房保卫战的标志性印象。这张相片不只定格了一位抗日名将的坚毅面庞,更成为我国军队现代化转型与民族精神觉悟的前史见证。
1936年,国民政府经过中德易货贸易进口31.5万顶德国M35钢盔,首要配备中心军的 “德械师”(如第87、88、36 师)。这种钢盔选用钼钢原料,内衬牛皮衬垫,是其时我国军队最精锐的单兵防护配备,谢晋元地点的第88师作为第一批德械师,全员配发该钢盔。
1930年1月16日,华盛顿特区的冬日阳光穿透白宫,这张宝贵的合影捕捉到了我国近代水兵史上重要的交际时间。杜锡珪带领的使团正在调查欧美日水兵制作经历,寻求技能合作或许,这一站,来到了美国,会晤美国胡佛总统。


相片是在暂时白宫履行办公室前拍照的,从左至右依次为:黄显淇上校、董显光先生、杜锡珪水兵上将、伍朝枢部长、程少校,两位美方伴随军官——M.H. Ching少校和T. De Witt Carr少校,别离代表水兵情报部与作战部。据《中华民国水兵部档案》记载,此次会晤继续47分钟,评论焦点会集在驱逐舰制作技能与潜艇防护战术。
这帧拍照于1954年香港英皇道兰心照相馆的张爱玲个人照,是文学史上稀少难得的视觉珍宝。

相片中,张爱玲身着一袭提花旗袍,高领如刃,宽袖垂落,在照相馆特有的柔焦灯光下,将东方女性的古典韵致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疏离感熔铸为永久的美学符号。最摄人心魄的是她的目光——单眼皮轻轻上挑,目光穿过镜头直射观者,似在审视浮世悲欢,又似在与三十年后洛杉矶的自己隔空对话,这种穿透时空的注视,恰与她自题的“怅望卅秋一洒泪,惨淡异代不一起”构成互文。

这张相片的诞生与张爱玲彼时的人生转机严密交错。1954年的香港正处于战后重建期,英皇道上叮叮车络绎,茶室飘出虾饺与奶茶的香气,而张爱玲租住的北角公寓里,堆满了《秧歌》英文本的校样。
1954年的张爱玲刚完结《秧歌》与《赤地之恋》,这两部以大陆土改为布景的小说在海外引发争议,而她自己正准备移居美国。这张相片后来成为张爱玲晚年最珍爱的印象,1984年她在洛杉矶收拾行李时偶尔发现。